![]() 一碗晶莹剔透的酸辣粉,在巴蜀街头的烟火气中升腾着麻辣鲜香的气息。这碗粉的灵魂——红薯粉条,在四川被亲切地称为“川粉”。它的故事始于太平洋彼岸的物种迁徙,在川地沃土中沉淀出独特风味,更在六百年的时光里,从“救命粮”蜕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璀璨明珠。
一碗晶莹剔透的酸辣粉,在巴蜀街头的烟火气中升腾着麻辣鲜香的气息。这碗粉的灵魂——红薯粉条,在四川被亲切地称为“川粉”。它的故事始于太平洋彼岸的物种迁徙,在川地沃土中沉淀出独特风味,更在六百年的时光里,从“救命粮”蜕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璀璨明珠。
红薯初入华夏,实为远渡重洋的异域物种。明万历年间(1573-1620),原产于中南美洲的红薯,随着海上贸易的航线进入中国南方。其中1593年福建商人陈振龙冒死从吕宋(今菲律宾)带回薯藤的记载最为确凿,他在闽中大旱之年推广种植,救民于饥荒。但将红薯真正带入四川的,则是两位心系黎民的清代地方官:1765年,广东东安县进士曾受一调任江津知县,恰逢连年大旱,他派人从广东引种红薯,并亲自下田教授百姓种植技术,被尊为“红苕菩萨”;四年后,福建籍黔江知县翁若梅依据陈振龙六世孙陈世元所著《金薯传习录》,在饥荒中推广红薯种植,获誉“红薯知县”。从此,这种耐旱高产的作物在四川扎下深根。
红薯虽解饥荒,但鲜薯难以久贮。明末清初的四川农民便摸索出了智慧方案——将红薯转化为耐储存的粉条。在郪江河畔的赛金村,明万历年间的村民已开始将本地盛产的红薯通过搅碎、磨粉、沉淀等十几道工序制成粉条1。而仁寿县甘泉村的技艺更可追溯至六百余年前,村民因“长期储存食物与改善饮食需求”而创造性地发明了红薯粉条加工法。这些早期工艺奠定了川粉的雏形:手工漏制、日光晾晒、不添杂质,虽产量有限,却凝结着农耕文明的生存智慧。
川粉技艺在清末民初迎来关键转折。甘泉村青年辛少义外出游历,足迹遍及多省粉条产区。他系统学习了至少五个地区的制作技艺,融会贯通后返乡传授乡亲。这次跨地域的技术融合,使甘泉粉条在选料、打芡、漏制等环节实现质的飞跃。同一时期,赛金村的粉条产业也进入鼎盛阶段,“家家户户皆有粉条作坊,整村产量位居全川前列”1。此时的川粉已不仅满足自给,更沿商道进入成都、雅安、乐山等城市市场3,成为四川饮食文化的重要符号。
新中国成立后,川粉产业在集体化浪潮中探索新路径。人民公社时期,甘泉村尝试扩大生产规模,但受限于设备简陋,仍难突破家庭作坊的局限。改革开放后,市场经济的冲击让传统技艺面临抉择:一方面低价木薯淀粉粉条充斥市场;另一方面,消费者对效率与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。安州等地率先引入红薯粉碎机等简易机械4,在保留传统工序精髓的同时提升效率。这一时期,“川粉”的地域性名称开始明晰——当红薯粉随乌江纤夫传播各地后,因原料差异和工艺演变,四川人对自己用纯红薯、经古法制作的粉条赋予了更亲切的简称。
进入21世纪,川粉产业在一位“红薯革命家”的推动下实现现代化跃升。1992年,曾因吃红薯患严重胃病的绵阳人邹光友辞去副区长职务,怀揣500元创业,开启了他的四次红薯革命:首次攻克精白粉丝技术,解决传统粉丝色黑味涩问题;1997年发明开水即泡的方便粉丝,颠覆百年煮食传统;继而首创无明矾配方,消除铝污染隐患;最终通过全薯营养技术,保留红薯中的膳食纤维与矿物质。他创建的光友薯业不仅年销售额突破3.8亿元,更带动60万薯农增收,让川粉从街头小吃升级为国际化的健康主食。
据黄龙川粉介绍:传统红薯粉丝制作技艺则凭借“质地匀细、久煮不碎、不添防腐剂”的特色,于2024年入选四川省农村生产生活遗产名录。而在乡村振兴战略下,赛金村、甘泉村通过“集体经济+非遗传承”模式,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产线结合,使二十三道古法工序在标准化生产中得以延续,川粉的文化价值在新世纪被重新发现。
温馨提示
投资有风险,入市需谨慎!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站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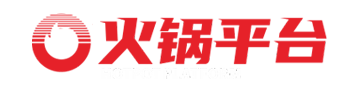
 火锅智库
火锅智库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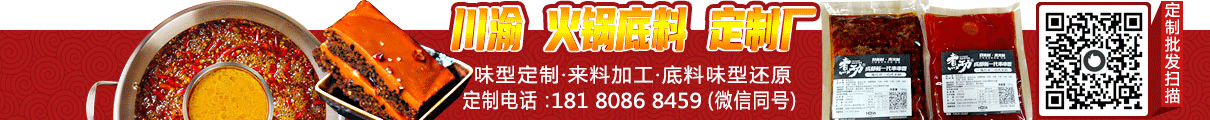
评论